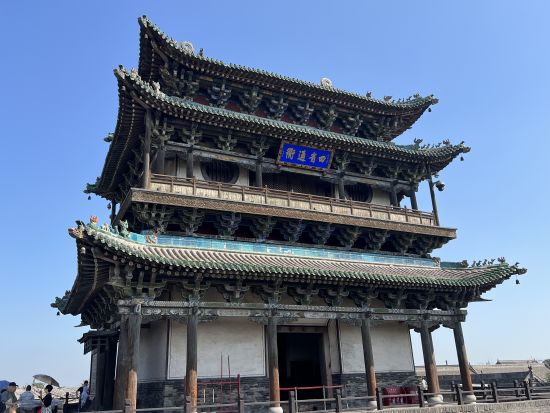曹建龍:爐邊閒話,暖透冬夜
稿件来源:菲律賓商報
2026年01月10日 00:44
冬天悄然而至,閒下來時,我裹緊衣領走在寒風裡,清冽的涼意撲面而來,腦海裡卻不由自主浮現出小時候玩雪的情景,心裡不禁漾起一陣暖意。
小時候,我喜歡下雪的冬天。霜降一過,天天盼著下雪。雪一落地,母親連夜搓好的草繩,緊緊捆在我的布鞋上,踏雪而行,踩出“吧唧吧唧”的聲響,尤為動聽。
我喜歡去村口的曬穀坪玩。那裡開闊,夥伴不約而至,吼著,鬧著,跑著,跳著,心裡那份快活,怎麼也訴不盡。
有一年冬天,雪下得突然,走去曬穀坪,見不少同伴穿著棉衣在玩雪,我一時興起,走過去,抓把雪就狠狠扔過去,對方也不客氣,捏個雪球砸回來。雪球在空中撞開,“啪”的一聲,雪沫子濺一臉,笑聲比什麼都響,傳得很遠。
雪花紛紛揚揚,有時隨風鑽進衣領,當即融化如汗,也不覺得冷。頭頂冒著熱氣,雪水和熱汗混在一起,流下來,心裡便有一種說不出的痛快。
玩累了,我就安靜下來,蹲在地上堆雪人。從坪裡各處把雪攏過來,先堆個胖身子,再捏胳膊和腿,安上一個圓腦袋,用黑煤渣當眼睛,插兩片樹葉當眉毛,連下巴的“鬍子”都捏得有模有樣。忙得滿頭是汗,棉襖都濕透了,也顧不上冷,還在埋頭擺弄,忘了回家吃飯。
“死仔,這麼遲了,還不曉得回家吃飯?”母親的喊聲從老遠傳來,話音沒落,人已到了跟前,一把拽起我的手就往家走。
回到家,我搓搓手,母親拎來烘暖的毛線鞋,換下我濕透的布鞋,嘴裡念叨:“瘋什麼瘋!真不懂事,鞋都濕透了,你看明天感不感冒。”說完就把濕鞋拎到火爐邊烤。鞋子冒出白氣,混著柴火的味道飄來,我心裡“騰”地一下就暖了。
冬夜裡最舒坦的,就是點起煤油燈,一家人圍著爐子閒聊。說地裡的收成,聊村裡的閒事,東拉西扯,沒個主題,卻越說越起勁。
說夠了,就各做各的事:母親洗完碗,搬個小凳坐在爐邊織毛衣,線團在腳邊滾來滾去;父親靠在椅子上打盹,嘴角還帶著笑,酣然入夢;我捧著一本書,就著那點昏黃的燈光,慢慢翻閱,偶爾抬頭,能看見母親手裡的毛線針在燈下泛起微光。
靜下來時,我總愛扳著手指頭數日子。一天,兩天,三天……從冬至數到小年,再數到除夕,越數心裡越滿是歡喜。除夕逼近,水塘抽乾了,大人小孩穿著雨靴踩進泥裡摸魚,笑鬧聲能掀翻屋頂;石磨“吱呀吱呀”轉個不停,磨出的豆漿做成白嫩的豆腐;殺年豬那天最熱鬧,半個村子飄著肉香;鄰里們湊在一起打糍粑,你一捶我一捶,喊著號子,忙得熱火朝天;門頂上掛起紅燈籠,紅綢子飄來飄去,年味就濃得化不開了。
有時夜深,母親還會從樓上拿幾個紅薯下來,煨在爐灰裡慢慢烤。烤熟的紅薯,外皮焦黑,帶著炭火的溫度。拿一個掰開,裡頭金黃軟糯,甜香直衝鼻子。咬一口,又軟又綿,甜汁順著嘴角往下淌,煙火氣濃濃。
冬天,是團聚的時節。不圖什麼好酒好菜,一家人圍爐坐下,東扯西拉,就是難得的溫暖。冬日裡最讓人惦記的,不是漫天大雪,而是記憶裡那團不滅的煙火氣,是吃上母親煨烤的紅薯,聽她和父親嘮叨家常的安心。
如今我住縣城,窗外的寒風呼嘯。路燈昏黃,照著清冷的街道。我望著漆黑的夜空,望向老家方向,有一種說不清的空落,此刻忽然明白,我想家太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