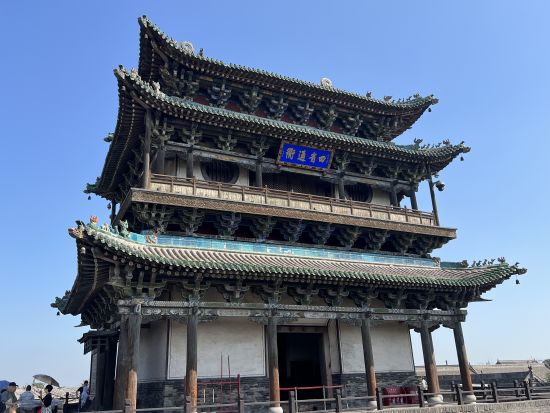陳理華:小寒尋暖
稿件来源:菲律賓商報
2026年01月09日 00:34
小寒時節回到家裡,雞叫頭遍時,窗外還是濃得化不開的黑。風“颯颯”地貼著窗縫鑽進來,氣息如浸過冰的綢緞,拂過面頰。我縮在被子裡打了個哆嗦,趕緊把腳往床尾特意備好的熱水袋挪去,緊緊貼著那點行將消逝的餘溫——這是南方小寒清晨,最直接的尋暖方式。小寒是全年最冷的時節,冷得凜冽又真切,而人們尋暖的腳步,早已跟著寒聲動了起來。
在村裡,農戶人家都起得早。我若是賴床,母親準會在屋外大呼小叫,讓人不得安生。硬著頭皮爬起來,裹緊棉襖推開屋門,寒氣便如浸透冰水的棉絮,呼地一下裹住全身,連呼吸都滯澀了幾分。院牆上的霧珠涼津津的,指尖一觸,涼意便往骨縫裡滲;牆角的枯草被風刮得東倒西歪,連麻雀啄食都縮著翅膀,不敢多耽擱。我沒多停留,快步折回屋裡——尋暖的第一站,從來都是飄著煙火氣的廚房。
屋裡早已被灶火烘得鬆軟暖和。母親正守在灶台邊,將幾根粗柴添進灶膛,“劈啪”的燃燒聲裡,火星子時不時蹦出來,轉瞬即逝,卻也捎來細碎的亮與暖。她握著長柄勺,緩緩攪動鍋裡的粥,白茫茫的水汽裹著醇厚的米香,一股腦往人身上漫。“小寒天,就得先喝碗熱粥,暖得能扛到開春去。”她轉頭衝我笑,用嘴努了努灶口:“過來烤烤火,驅驅寒。”我趕緊湊過去坐下,伸手攏在灶口,凍僵的手背被火舌舔得又燙又癢,蜷曲的指尖慢慢舒展開來。順手拿起灶臺上的橘子,在火邊暖了暖,溫熱的橘瓣剝開來,甜香混著一縷暖意滑進喉嚨,一股紮實的熱流便在胃裡漾開——這是家人用柴火與時光釀出的暖,尋得踏實,落得妥帖。
身上剛聚起的一點暖意,一出屋門便被風吹散了大半。我縮著脖子往村口去,卻見那裡早已聚起了一團光與熱。大爺們搬來椅子,圍著旺旺的篝火,將自己安放在冬陽與火焰之間。每個人都裹成厚實的棉團,雙手攏在火邊,像是要從那跳躍的光裡捧住一份固體般的溫暖。旱煙袋“吧嗒”著,煙圈混著熱氣慢悠悠地飄;閒談的話語裹在暖霧裡,語速也慢騰騰的,自在得如同田埂上散步的雲。我湊過去烤手,一位大爺用樹枝從火堆裡扒出個黑乎乎的烤地瓜,在地上熟練地翻了幾個身,才遞過來:“剛烤好的,暖手又暖心,小心燙!”我接過來,雙手不停地倒換著那滾燙的溫暖。剝開焦脆的外皮,金黃的瓤子冒著誘人的甜香,咬一口,溫軟的果肉滑下喉嚨,渾身的寒氣似乎都被這口甜蜜逼退了大半。另一位大爺往火堆裡添了柴,指著田野上閃閃發亮的霜說:“你看這霜,結得多厚實。天越冷,明年的害蟲就越少,莊稼就越有精神。咱們守著這堆火,心裡就越亮堂。”大傢伙兒聽了,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來,笑意在火光映照下暖融融的。
我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,一丘丘收割後的稻田里,稻茬上的薄霜像撒了一層晶瑩的鹽,陽光一照,泛起細碎而清冷的光。原來這小寒的霜,竟是越厚越好,它凍殺蟄伏的害蟲,也默默積蓄著地力,靜待春生。鄉鄰們聚在這火光邊,用陪伴與閒話尋來的,便是這熱熱鬧鬧、可握在手裡的慰藉。
傍晚,山風更緊了,臘肉的鹹香、燉菜的濃香,在清冽的空氣裡勾出一道道溫暖的軌跡。一家人早早圍坐在方桌旁,蘿蔔燉羊肉在砂鍋裡咕嘟著,熱氣模糊了彼此的臉,卻讓心貼得更近。羊肉湯醇厚,喝下去,一股暖流從喉嚨直抵四肢百骸,驅散最後一絲寒氣。酷似父親的弟弟抿了一口白酒,咂咂嘴說:“這天兒,就得吃點熱乎的,喝點暖身的,人才舒坦。”我捧著溫熱的湯碗,指尖被焐得微微發紅,連呼出的氣息都帶著滿足的暖意——這是家人圍坐,用熱食與相守尋來的暖,安穩、踏實,足以抵禦窗外任何風寒。
夜裡,風仍在窗外嗚咽,我卻裹在曬足了太陽的棉被裡,被一種乾燥而蓬鬆的暖意包圍,很快便有了睡意。窗外是簌簌的風聲,屋裡是家人均勻的呼吸聲,空氣中還交織著臘肉、米飯與陽光的餘韻。原來,小寒的冷,從不是單調的蕭瑟。人們以炊煙、以爐火、以閒談、以共食,在凜冽中開闢出一方方溫暖的據點。那灶邊跳動的火光,村口聚攏的篝火,桌前溫熱的湯羹,無一不是平凡日子裡熱烈的生存智慧,是對嚴寒最溫柔也最堅韌的回應。冷得真切,才襯得每一份尋得的暖,都如此實在、如此珍貴。這便是小寒最動人的模樣,是紮根於泥土、升騰於煙火的最踏實的歲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