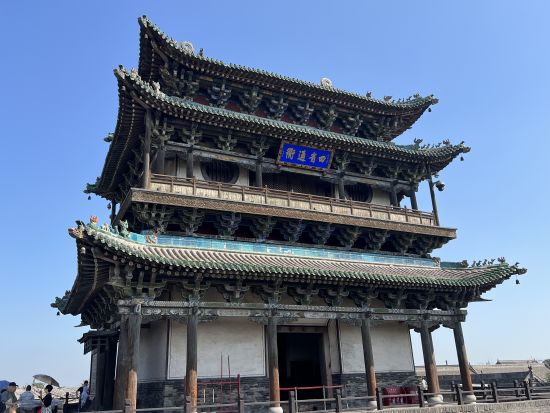吳奮勇:古榕山水意
稿件来源:菲律賓商報
2024年10月31日 00:21
農村老話常說:“無樹不成村”。有村必有樹,樹是村莊的景致和氣場。
我生長的地方叫亭後,背靠石竹山,又名石竹岩,地圖上這樣標注,縣志裡也有記載,而村裡人習慣叫它“茶箍尾”,也許是因為它的山巔至今還有幾壟茶園的緣故吧。登臨它,盡覽蓮花山和泉州的母親河晉江西溪;遠瞻聞名海內外的清水岩。我們聚居在半山腰,我曾稱說是掛在半山腰的小山村。村裡有多少種草木,多少棵樹,誰也數不清,而有林業部門掛牌的古樹只有兩棵,是村裡的“樹王”。
一棵在茶箍尾的山麓,是榕樹,村裡人叫它“山腳榕”。在一座房屋的後面。村裡口口相傳,說是主人建好它後才種下這棵樹,樹上有一個2016年掛的牌子,寫著樹齡260年。老房子,“十間張”建構,兩邊有“護厝”,石基土牆青瓦,四周雜草萋萋,木門敞開,如今無人居住。看上去,比古榕年輕,我猜想,也許是主人不知從哪裡移植而來的。我和這棵樹有深厚的感情。樹下是一個小操場,小操場的後面是一座房子,我小學一、二年級就是在那就學的。那時有兩個班,是複式班,唯一的老師是我的父親。樹上掛了一個老舊的犁耙,旁邊拉著一根繩子,綁著一根鐵條。站在下面一拉,就可打出聲音,就是所謂的上學和放學的信號。如今沒有琅琅書聲了,村裡人還津津樂道,這裡走出一個清華學子、兩個博士、三個研究生和五個校長書記。有時村裡要開會,集合,也會敲著它。這棵樹的根裸露著,一條一條的,有分又合,連成一片,匍匐在亂石上,猶如生出利爪抓住石頭,石頭間長出野草,開出花,小而美。那時,我們四個同齡人以生產隊裡刷牆壁用的“大板椅”作為課桌,手拉手剛好把它的底頸團團圍住。這部分有一米來高,然後開始分枝,先有三分叉,其中靠山一邊的兩叉再各自分叉,剛好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有,向上生長,鬱鬱蔥蔥,亭亭如蓋。我曾爬上去,去採“寄青”,也望村莊,一覽無餘,特地往茶箍尾山望去,一派繁盛,扶搖而上。
另一棵也是榕樹,佇立在一個俗稱漈頭的地方,已經220多歲了,沒有長成如蓋的樣子,樹根攀爬在一塊大石頭上,向東南方向稍傾斜而上,兩米左右處分三叉,一叉往東南方向伸出小小一段就開始往四周不均勻地分支,像一把扇子。另兩個分叉主幹勇敢地向空中發展,旁支不多也長得慢。如今,它的靠地面部分爬滿籐蔓,去年起我去的時候,發現一朵菇類,黑色的,臉盆般大,我用了很大的力氣都搖不動。樹的旁邊是山澗,俗稱“坑溝。”村裡人叫它“水邊榕。”這條山澗細水長流,源頭是一個叫冠厝的地方,那裡有一個水庫,碧波蕩漾,水草豐美。這條山澗穿過村裡大部分的田地,是村莊的“生命線”。樹下是一個六十米左右的山崖,雨季時瀑布飛瀉,氣勢磅礡。平時水量小,落到石壁和潭裡,聲音響亮。老一輩人比喻說成是“如敲銅鈸”。樹下自然天成,拱出一個洞,可共兩人棲身,洞口有一條狹小的路。古榕的左邊是一片田地,一層又一層,每層只有一兩米寬。聽祖母講,我們村裡的有一個人漂洋過海的人回來了路過這裡,就坐那大哭。他說,他就是那樹洞裡出生的,搖籃血跡永不忘,夢裡樹大抓不著。一條石級路,蜿蜒而上,就在田地旁,在樹下繞出一個“S”彎,是我們穿越村莊的必經之路。聽村裡的老一輩人講,以前南安蓬華人要到蓬萊清水岩會路過我們村,時常有人在古榕樹下休息,村裡人在那裡弄了一個茶水點,無償供應。一杯熱茶溫暖了一顆顆虔誠的心,助力前行的腳步。
兩棵古榕樹,一高一低,相距一百多米,遙相呼應,幾百年不變。之間有一處較平坦的地方,有兩個大埕,青草石為岸,裡面灰白,無比空曠。以前生產隊時曬稻穀、小麥、豆類等,旁邊建了兩座倉庫,白牆青瓦,木門雙開,村裡放電影、開會都在那進行,是村裡的經濟文化中心了。現在,倉庫不復存在。30多年前,眾人合議在大埕中央建設保定宮,從此成為村裡民俗活動的地方和停車場。站在這裡,可以平視山腳榕,若如撐開的巨傘,欲與群山比高;可以俯瞰水邊榕,像一把利箭,叱吒風雲,指向高遠。
樹是大自然饋贈的綠色寶藏,綠樹和山水互為映襯,豐富了鄉村的四時之美。兩棵古榕更是人與樹和諧相處的見證。我的鄰居是一位攝影愛好者,把小山村拍個遍,做成了明信片,原來我們村也這麼美!出門在外的人,喜歡懷揣家鄉的照片,在異鄉奔波,兩棵古榕是照片主角。我把這事講給妻子聽,愛好美術的她也愛上它們。前年夏天,她特意回家寫生。我把她的畫,掛在書房。每當看到它,我好像回到老家,在青山綠水間奔跑,在田間地頭佇立,在古榕樹下遐想,做一個永遠長不大的鄉村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