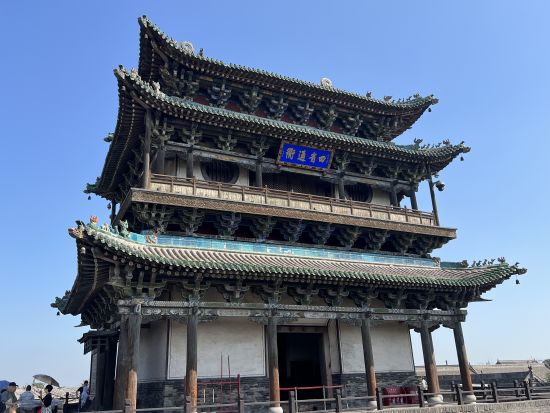胡武勝:春雨入江南
稿件来源:菲律賓商報
2025年04月12日 00:16
徽州的春雨像是松煙墨潑進了山水間。臨近午時,江上已浮著些零星的雨腳,我披衣在窗前站了會,雨絲就稠了起來,家家接連升起的炊煙,將要貼著雨絲往上爬,總被江風揉碎,氳進了墨色的山水,雨珠子斜斜掃過馬頭牆,簷角的鐵馬也叮叮咚咚地搖起來。
幾葉烏篷船緩緩靠岸,遊客說著笑著下船離去,老楊頭倒還調轉船頭,往江中漂去,“去家吃飯啊!”“春水船如天上坐!”老楊頭話音未落,小船已搖著頭扎進江霧裡。新安江邊好些渡口,一入了春,遊客就密了,老楊頭年近七十,好些年前在江邊打魚賣魚,撐得一手好船。
“老楊頭又喝酒去了。”這時候的水路最宜淺酌,兩岸山色像是被雨絲勾了層淡赭。船過江心,老楊頭把木漿隨後一放,從船板下摸出個錫壺,就著花生米,慢悠悠地品起來。我頭一次見這錫壺,是攜外地朋友感受徽州的春色,正聽著竹篷上響起細細的沙沙聲,兩岸桃花梨花交相盛開在雨幕裡,朋友驚歎連連,激動中一抬手,掛在竹篷邊的錫壺便砸了下來,漏出的酒香惹得老楊頭不住地歎惜。朋友下船時掏出好幾斤酒的錢遞上去,老楊頭連連推脫。後來的幾天,朋友堅持走水路遊玩沿江,因此跟老楊頭漸漸熟絡起來。
雨絲順著窗縫鑽了進來,澆在臉上涼津津的。三五個戴著箬笠的姑娘蹲在埠頭,正往竹簍裡碼著洗乾淨的蕨菜,遠處不知誰一聲口哨響起,雨霧裡忽然游出一隊鴨子,領頭黃鴨的翅膀撲稜稜打散水面,攪碎了倒影裡說笑的姑娘面龐。
雨歇時分,青石板路泛著幽幽的光,從路口蜿蜒著鑽進深巷。牆根下絨絨的苔蘚,被瓦片滴下的水珠鑿出淺淺的窩。牆上半截櫻花探出頭來,粉粉嫩嫩,忽聽得吱丫一聲,對門漆色斑駁的木門打開,露出個竹編的簸箕,鋪滿了剛出鍋的筍片子,哄哄地冒著熱氣,頭戴布巾的阿婆兩手向前撐著簸箕,正吃力地喊著什麼,木門裡就竄出一個孩子,拽著兩條小板凳就跟了上去。
不遠處支著油布棚的老攤子飄出煎毛豆腐的焦香,油花在雨氣裡滋滋地跳,鍋面排開方方正正的毛豆腐,白絨絨的菌絲好似落了層新雪,邊角已叫菜籽油煎出焦黃的脆皮, “急不得,要等這‘虎皮毛’生全咯!”攤主用鐵鏟輕輕撥弄,豆腐塊上的絨毛在熱油裡蜷縮成金絲的網狀,刺啦啦騰起的香味勾得幾個路人不肯離去。朋友第一次吃毛豆腐時,抱著試毒的心態久久不敢下筷,咽完了頓覺香氣撲鼻,“這香味真怪,三分像松菌,七分像奶酪的醇。”嘗過洋墨水的朋友一開口就讓這毛豆腐第一次有了異域的香味。
街邊采風的幾個學生撇開手裡的畫,眼巴巴瞅著攤主撒一把蔥花,捻出毛豆腐壓在瓷碟裡,澆上兩勺辣醬,看著紅油慢慢滲進蜂窩狀的肌理,外皮脆如春卷,內裡卻滑似凝脂,一口咬下,後頸立時沁出一層薄汗。一陣風吹過,簷下滴落的雨珠劈啪啪砸進油鍋,炸開的油花嚇到了竹匾裡打盹的貓,“喵”一聲驚呼縱身下地,卻碰翻了晾在窗台的豆腐乳,幾名學生也怏怏地跑開。
江對面的茶山隱隱浮在雲霧裡,幾名採茶的婦人裹著藍布頭巾,身影被霧氣洇成深淺不一的青。小時候最怕採茶,天幕未亮時,茶簍碰撞聲就已撞碎了茶山的夜色,陡坡的茶樹掛著宿雨,採茶人一個個將身子弓進茶海,露水順著葉脈灌進袖管,後脊樑沒一會就叫衣服糊在背上,昨日的茶漬早把手指染成赭色,變黑再至指甲和皮膚浸成墨,許多年後我的食指和拇指仍要比其他指頭顏色深些。
暮色垂下,燈籠一盞接一盞亮起來,映得青石板泛著蟹殼青的光。
“魚躍龍門!”鑼鼓聲遠遠傳來,孩子們的叫聲越來越亮,一陣紅鯉的魚燈破開喧鬧從巷弄湧了出來,幾十盞魚燈描著金邊,舞起來真似金龍擺尾,領頭的金鱗巨鯉足有三四米高,口中銜著的寶珠竟真能隨著魚頭擺動吞吐明滅。“鯉魚戲水!”魚腹內的燭火將人影投在粉牆上,一陣祝禱聲裡,魚燈齊刷刷昂首躍起,竹篾編的鯉魚鬚子顫巍巍掃過馬頭牆,鱗片上貼的金箔映得滿街生輝。
江霧不知什麼時候散的,樓下酒坊支起木窗板,糯米酒香混著潮氣,把暮色釀成了琥珀。遠遠望見老楊頭蹲在船頭修補罩網,網眼間漏下的月光像是撒了把碎銀。深巷裡飄來烘茶香,該是哪家乘著月色趕製新鮮的毛峰。“小樓一夜聽春雨,深巷明朝賣杏花…”誦讀聲裹著花香鑽進窗柩,散在小城的燈影裡。